
 手机版
手机版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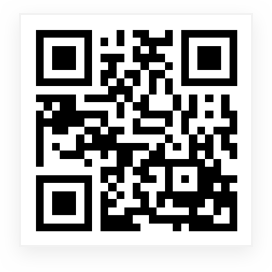
当前,全球经济处于新一轮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的关键发展期,以大数据、云计算、区块链、人工智能、5G为代表的前沿技术与新型互联网模式交织演进,不断推动先进科技的产业化应用,新技术催生的颠覆式创新层出不穷,传统产业链体系逐步崩解重构。在此背景下,出版业进入增长乏力和业态转型的阵痛期。面对多重挑战叠加的行业板荡,出版人普遍感到焦虑、无力,凸显难以适应行业之变的艰难困境。
我们知道,互联网经济模式的主要特征是:实体+数字空间、共享平台,充分竞争,大数据驱动,不断迭代。互联网构建的统一大市场,数字技术对信息流、物流、资金流的全面赋能,新介质,新技术,新渠道,新组织,新业态的创新与组合,不断创构新的产业价值链体系。而传统出版业由于体制机制原因,不同程度存在产品和渠道垄断、条块分割、市场竞争不充分、与相关产业的相互渗透不足,与新型要素市场缺乏连接等问题,呈现一种长期的行业封闭性,这恰与互联网经济的开放性构成了一对矛盾,表现出对新技术新模式敏感度低,畏惧变化和竞争,习惯路径依赖和政策保护的舒适区。
究其本质,是对以数字化、信息化、智能化、交互式为特征的新型出版产业体系认知不足,技术突破、互联网大市场的形成、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,不断催生新的供需、新的市场、新的产品、新的组织,不能用老经验、旧眼光看待正在发生的行业变革。无论新质生产力还是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,其承载主体都是新型出版产业体系,因此,推动出版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,要放到技术革命的大视野下,重新辨析、界定出版业生产要素优与劣、变与守、快与慢的内涵,推动产业尽快融入实体和数字融合共生的新业态,找准发力点,创造新利基。
01内容产出模式渐次从PGC、UCG、AIUGC迈入AIGU时代
内容是出版价值链的核心要素之一,在传统业态下,内容的获取、加工、分发、变现表现为单向、封闭、低效的特征。近年来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积累与模式迭代,内容资源的产出出现革命性变化,呈现如下演进脉络:
第一阶段,从PGC(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)到UGC ( user generated content ) 。传统出版的内容来源,主要仰赖作家、学者等专业人士的著述或传统媒体的内容再开发,各大新兴互联网平台自制版权内容的二度开发也多可归入此类。随着交互互联网的快速迭代, UGC模式逐渐兴盛,即用户生产内容。这些互联网平台海量的写作者、大v、流媒体IP、mcn机构源源不断给出版带来新的内容产出和选题储备,但人人皆可作为用户生产内容实质也改变了出版的形态。
第二阶段,从AIUGC (artificially intelligent UGC)到AIGC (AI-Generated Content 生成式人工智能)。AIUGC是人工智能与UGC的结合,人工智能参与到用户创作内容的过程中,使创作的便利性、数量、质量得到极大提升,但人工智能更多是作为一种效能工具为创作赋能。
ChatGPT、GPT-4大模型的横空出世,使内容生产进入AIGC的尖峰时刻。AIGC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自动生成内容的生产方式,与PGC、UGC和AIUGC不同,人工智能取代人类,成了完全的内容生产者,可以不舍昼夜地生成文本、图片、音视频等多样化内容。在大数据、算法和算力支撑下的大模型具有异常强大的功效,在更多场域代替人类进行创作生产,在数量值、多样化、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等方面已远超人力,必将推动内容生产的巨“大跃进”,也将催生更加多样的内容形态、精准锁定用户需求极具性价比的产品以及创新变现方式。AIGC势必对传统出版内容获取和内容变现造成颠覆性冲击,在大部分文教、知识变现场景中将对传统出版发生替代,也会发展出完全不同的新需求、新场景。在AICG时代,产权的边界、商品的边界、出版的边界都已漫漶不清,出版竞争已不再是行业内的竞争,基于内容的产品和应用,其场域将远远突破传统出版的边界,与其他相关行业形成勾连交融。因此,出版如何重新定位,如何趋利避害重组产业价值链体系,需要出版界高度重视,并提前加以研究与探索。
02纸书渐趋式微,介质的多元融合与元宇宙场景开拓出版新疆域
纸张作为出版主要介质绵延久远。纸张的发明距今已逾2000年,活字印刷术诞生超过1000年,即便西方发明现代印刷机,也已过去了200年。以纸张为介质传播、积累知识文化,提供精神娱乐的范式终于迎来千年激变。可以预计,纸张和书本作为出版主要介质的时代正走向终结,这个过程或许还需一两代人,但改变已然发生,结局几无悬念。出版人不必为纸书的落日慨叹惆怅,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正为出版打开另一扇门。
从现阶段看,内容资源的多介质分发,主要形态为图书、电子书、有声书、多媒体衍生品、游戏、影视化改编等。尽管目前支撑产业存续还主要依靠图书的规模与利润,但须注意的是,新技术的迅速跃进,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 、虚拟现实、增强现实技术、元宇宙、数字人和区块链应用的迭代成熟,内容经营的形态和模式不断演进,使内容出版介质的样貌和应用场景展现新的气象。试举几例加以说明:
第一,跨媒体融合出版物。出版物将不再以单一介质形态呈现,而是融合不同介质形式,如文字、图片、音频、视频的叠加组合,以适应不同平台、设备和使用场景的需求。
第二,元宇宙出版物。利用元宇宙中AR、VR、XR技术,为读者提供全方位沉浸式阅读体验。例如通过AR、VR技术重现内容场景和人物,读者佩戴VR设备,进入虚拟空间,与人物互动,身临其境感受作品魅力,增强阅读的趣味性和互动性。VR体验不仅是视觉上的感受,还包括听觉、触觉,甚至嗅觉元素,可以创造一个全感官的沉浸体验空间。
第三,数字人出版物。利用数字人技术开发互动式产品,读者与数字人角色进行交流互动,参与故事情节的创作,影响故事发展的走向。这种产品形态还可以打造数字人IP形象,创造新的商业应用价值。出版机构还可利用数字人技术创建虚拟课堂和虚拟导师,用于在线教育、知识分享、课程分发、积累私域流量。具有IP属性的跨媒体数字人,还可用于影视、动画、游戏和直播带货,实现不同场景的商业变现。
第四,NFT(区块链)出版物。NFT技术不仅可以用于出版物的唯一性标识和版权保护,还可满足数字内容的独占性和收藏性需求。特别是具有IP属性的内容资源通过NFT的发行,出版物可以具有更高的传播价值和收藏价值,使读者拥有属于自己的数字资产。
03破除路径依赖,新渠道运营能力已成为出版机构核心竞争力
渠道通常指商品或服务从生产者到最终消费者的转移路径,也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。商品到货币那“惊人的一跃”要依靠渠道实现,它是产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环节。
可以说,传统出版最具路径依赖的就是渠道。图书是少见的统一标价商品,这种定价形式的存在,在于图书产业链上下游具有较稳定、简单的(折扣)分配机制,基本保障了产业链各环节滚动经营、资本积累的需要。但互联网经济闯入书业的“禁地”后,一切都发生了改变!
首先,图书作为低价值标准化商品,被互联网业态所青睐,图书的统一标价方便平台比价,质量稳定易鉴定,无保质期和保修问题,物流损耗率低,它还具有小商品的多样化和复购率高等优点,特别适合作为互联网平台的低价导流品。近年来,互联网平台的恶性竞争,加之市场监督和行业自律的缺位,图书的乱价和低价倾销使出版业的利润空间被消弭殆尽,图书产业的生存与发展受到巨大挑战。
其次,从行业细部观察,近年伴随通信和互联网技术进步,各种电商模式不断兴起,叠加疫情冲击,人们消费图书的习惯已不可逆转地从线下迁移到线上,实体门店销售规模持续下滑,门可罗雀。同时,线上模式也不断演化,从平台电商、垂类电商、社交电商到短视频电商,流量在不同平台间快速迁移,消费者分众集聚在不同的数字空间。这种渠道的裂变、去中心化,导致内容各异的图书难以找到适合的渠道和消费人群,销售集中在少数爆品,网店长尾效应递减,营销管理成本不断上升,销售具有高度不确定性。传统出版机构业务架构、组织形态若不迅速做出反应,就会很快被市场所抛弃。
渠道的新旧切换和图书售价的不断滑落,实质体现了互联网经济的关键特性,智能手机的普及、没有地理界限的线上市场使消费者具有比价便利,价格杠杆成为电商平台竞争的主要利器。在数字空间中,消费者集聚规模之大,信息传播速度之快,有利于打造高性价比的爆品,从而获取规模效益。因此,出版机构的新型渠道能力不仅在于拓展渠道数量,更要求出版机构具有与新型渠道相匹配的内部组织形态和产品能力,即持续打造高性价比爆品的综合能力。
04新型组织形态是构建新产业体系的黏合剂和发动机,精益化经营是出版转型的必由之路
企业组织形态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交汇处,合理、高效的组织形态可以更好地激发生产要素的潜力,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,进而提升企业的整体竞争力。
传统出版的组织结构是基于产业链分工协同的科层式结构,在企业内部的横与纵,企业外部的内与外,均过于强调板块的专业性和管理的边界感。由此催生出员工只对自己手上的工作负责,而不对企业经营最终结果负责的现象,严重的会出现“部门墙”。企业对外部变化反应迟钝,信息在内部流动不畅,难以形成有效的竞争力。这些现象和问题也是传统出版机构普遍存在的痼疾。
我们常说,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,这是数字时代的经济规律。新型组织形态不仅要适应变化,还要主动从变化中发现商机,组织需要具备高度的敏捷性和协同能力。出版机构的组织形态必须以用户需求为中心,以互联网化为目标,使组织结构具有去中心化和开放性特征。在这样的组织结构中,信息流向不再是单向或双向,而是网状的,有利于迅速掌握信息,快速做出决策,并穿透组织内部的管理边界,调度所需资源,满足渠道和客户的多向度需求。
新的组织还应具有自组织形态,建构具有负反馈调节机制的管理体系,自动裂变成长。
建构新型组织形态需要以适配的经营理念为先导,在出版业转型的当下,应大力倡导精益经营理念,就是把企业进行的各项活动,使用资源的数量(包括时间)最小化的经营理念。在企业内部消除一切形式的浪费或无效劳动,具备成本竞争的基本能力。数字经济的本质就是通过技术进步,提高各种要素的效率水平,在数字空间里,所有产品都在同台竞争,只有手握价格杠杆,专注用户体验,具有制造高性价比产品的能力,才能收获网络无远弗届的规模效益。换言之,一个出版机构没有优良的成本控制力,也就基本失去了在行业转型期趋利避害,脱颖而出的可能。
05出版新质生产力需要大量战略型、应用型、复合型人才
出版产业在数字化、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趋势下,需要一系列新型人才来推动持续创新,重塑产业生态。新型出版人才不仅要掌握传统出版的专业技能,还要能运用新理念、新技术、新工具满足行业蜕变发展的需求,他们的劳动对象由单纯的文字或图书,转变为多元融合的数字化产品和大量数据信息,其劳动工具不再是传统工具而是各种新型应用技术,他们在更加丰富多元的工作场域创造性劳动,为出版行业开辟新的生存空间。
因为新型人才的加入,出版业因此更具开放性、个性化,它会与各种前沿科技、应用场景、内容产出方式交汇融合,形成精彩纷呈,形态各异的样貌,有的更趋向技术主导,有的重在市场运营,有的突出IP价值……技术与市场的结合不断催生新的商机。出版企业需要具有跨行业视界和战略思维的领军管理者、敏锐市场洞察力和资源组织能力的跨媒体运营人才、驾驭新技术工具推动持续创新的技术研发人才、具备跨文化交流与合作能力,推动中国出版“走出去”的国际化人才等等。
总之,新旧出版的差别根本上体现为劳动者整体素质的差别。出版产业“出圈”发展与其他相关产业融合连接,需要更多复合型、专业化、个性化的新型人才。
06新质文化力是出版的内核,“文化+科技”是出版新质生产力的双引擎驱动
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3月在湖南考察时提出了文化与科技的“融合命题”:“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,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,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。” 总书记关于“文化+科技”的新思路,表明高品质文化产品能促进高品质的消费,从而拉动相关产业的高质量发展。以文兴产,科技赋能,无疑给出版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指明方向。
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标识,是出版的源泉与魂魄,出版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和途径,也是文化转化为生产力的重要一环。出版的新质生产力归根结底是一种新质文化力。我们强调科技创新的同时,切不可忽视文化作为出版内核的主体性。优秀文化需要新的叙事方式和展现形式,科技为文化的传播搭建了更宽广的平台和通道,为文化的创新性表达带来全新的体验。正是科技与文化的双向奔赴,给新型出版配置双轮驱动的强大引擎,共同塑造富于时代创意、多彩多姿的文化产品,为更生动展现博大精深、立体多元的中国文化提供了无限可能。
这也正是出版业涅槃重生的光明前景之所在。
(本文作者杨政,天地出版社社长)